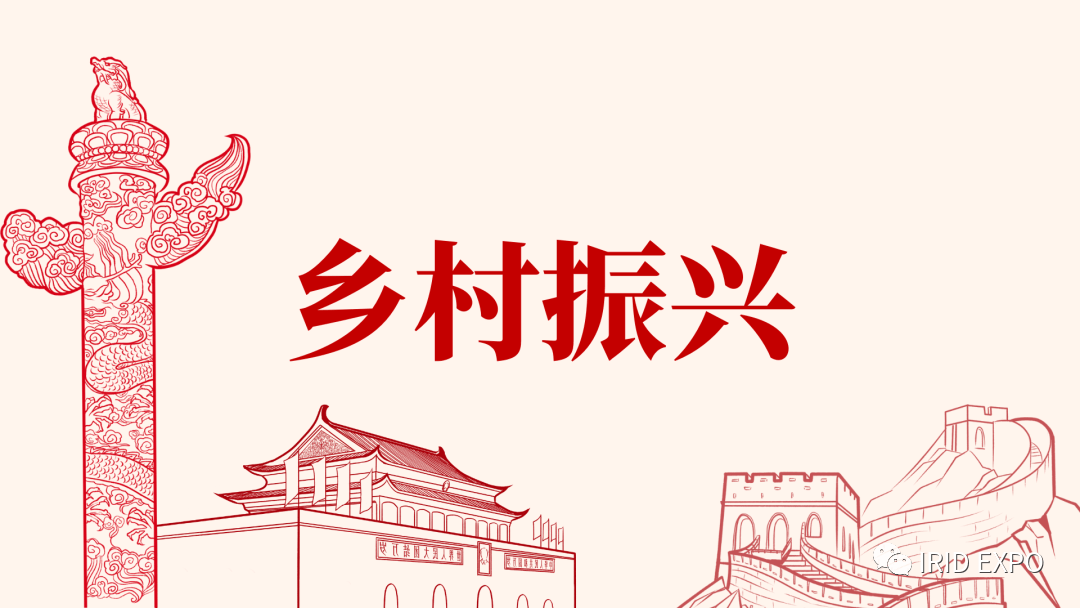贾林州:一号文件意味着我国乡村再工业化大幕拉开
編者按:
1978年改革以后,隨著人民公社體制的制度紅利在1978-1998二個十年經濟周期中耗損殆盡。土地集體所有快速走向類私有制,集體被瓦解,村社制度內部化小農生產與工業化外部成本的能力完全消失,村社成本及工業化、城鎮化的外部成本——三農問題,迅速成為中央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。
實際上,三農問題如果不能在農村化解,那么它就要進城。農業的糧食安全問題——由于村社集體瓦解,大包干的小農經濟造成的技術進步效率損失和村社組織效率損耗,是造成今天我國農業效率(國際競爭力)低下和結構性問題突出的制度根源——是進城的第一個重大問題。
總結改革前后三十年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,建國后土地集體所有為核心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,極大地重建了中國的農業生產效率,極大地重建了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社會效率。相反,大包干改革后的三十多年,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削弱和村社制度瓦解,都是極大地降低這二大效率。
今天,站在政治經濟新甲子周期的歷史起點,重建村社集體,都將極大地提升中國的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率邊界。
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,重建村社集體,是要改革大包干制度,加強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化能力,建立以村社集體為核心的土地經營制度,重塑集體與農戶的經營協同關系,最終重建土地集體所有制為核心的農村基本經濟體制,形成以村社集體經營為核心的鄉村生產、供銷與信用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合作經濟體系。
在農業產業方面,小麥、水稻、玉米、大豆等大宗領域,以村社為核心推動托管的社會化服務,突破小農經濟實現土地規模化,才能建立高效率低風險結構的農業經營體系。以合作社或社會資本企業為核心的土地托管,受制于地方性水文土壤等信息、氣候風險、勞動成本及地租剛性結構等因素,根本不可能大規模推廣,更不具備效率優勢,因此不可持續。
如果政策推動非村社力量推動土地托管,來實現規模化,那么可以肯定,中國糧食總進口比率上升的開放缺口根本不可能收斂。其后果,將會很嚴重。
在工業化方面,推動村社集體化,將為近3億多奔波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節省每年夏秋二季約20個工作日的農業投入時間,增加城市和工業勞動供給總量5%左右。更重要的是,這還將為另外3億多在農村生活的半勞動狀態的勞動力,在鄉村集體工業化的進程中,提供勞動參與的廣闊機會。
總之,村社集體化,將大幅提升中國工業化的勞動供給規模,極大地改善中國工業化的邊界效率,重塑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,大大加強中國工業全產業鏈的基礎性能力。
是的,有了具備價格優勢的集體土地,有了具備價格優勢的勞動要素,鄉村振興戰略下的中國鄉村,已經站在再工業化的歷史起點上了。
推動村社集體化,就將開啟中國鄉村4億人的工業化進程。無論如何,4億人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,將再次釋放中國經濟未來三十年的8%的中高速增長潛力。而重建村社集體將構筑良性循環的城鄉關系,將大大拓展中國經濟增長的高度與長度。
如不出意外,三十年后,中國經濟將重回約占世界經濟總量4-5成左右的歷史常態。
須明白,只有村社集體化,才能開啟中國鄉村百萬億級的資產證券化進程,才能形成對美元資本倍而圍之的競爭優勢。
更須明白,只有村社集體化,將愛人之仁與為民之義的倫理真正落地為有效的制度設計,讓農民合理分享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歷史紅利,人民幣才真正延續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合法性,才真正具備了仁義的哲學倫理,進而才真正形成上下同欲的合力,才真正具備高效率的備兌物質基礎——建立在村社高效率生產和制度能力基礎上的物質基礎。
信用貨幣時代,基于高效率農業生產制度的宏觀經濟增長周期,是維系貨幣長周期穩定和升值,并依貿易體系向全球流動的即貨幣國際化的決定性條件。
我們必須清楚,我們的貨幣叫人民。組織化的村社集體制度,才是人民國際化的基礎性制度條件之一。
作為偉大的政治家,習近平總書記非常明白,重建村社集體,是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使命。因此,早在2006年,他就在浙江瑞安做“三位一體”的綜合農協試驗,重建以村社集體為核心的農村合作經濟體系。
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。歷史期待鄉村振興戰略,重建村社集體,開創新的歷史局面。這是人民的心聲。